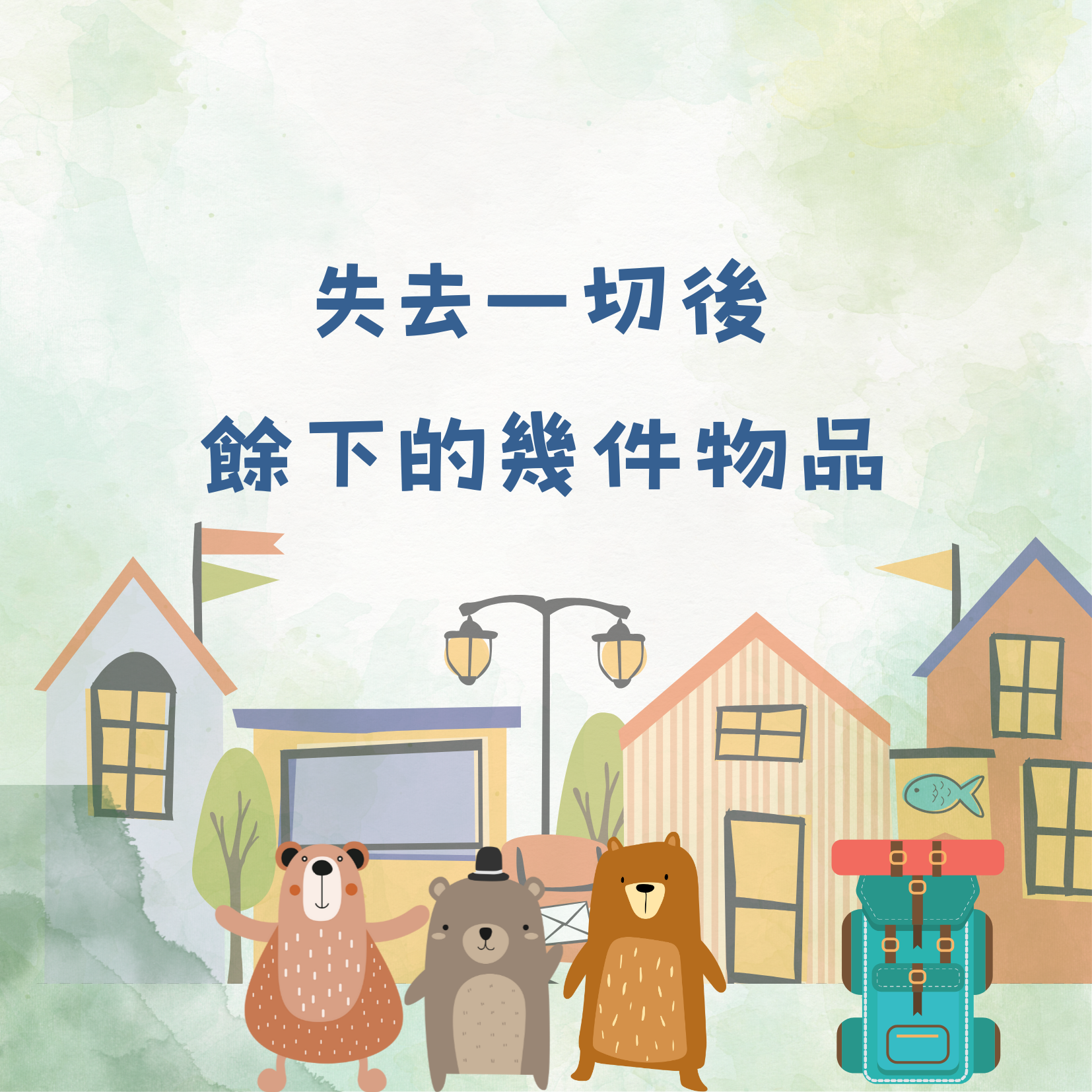作者:侍夜紫
我原本的生活,是有著小康的家庭,家裡有電腦、烤箱、床、衣櫃、鞋櫃,還有好幾雙鞋子,以及長年慢慢累積的烘焙玩具。在家裡,常常有零食,心情好也可以自製甜點。兩年前12月,股票一直跌,行情普遍不好,爸爸被錢逼瘋了,我們拿他沒辦法,平日他把家裡放得很滿,已經壓縮到生活正常水準了,他買了4箱名片,讓家裡的空間小到沒有辦法坐椅子,沒辦法玩烘焙,還得幫他做出靈芝糊出貨,而爸爸不太支薪給我。
每每我被鼓舞要找工作後,總是會出現客人追加訂購靈芝糊,爸爸退休後,沉迷抖音,看高張力短影音影片,劇情總是在吵架的那一類,加上是聲音外放,所以家裡就會很吵,影響家人睡眠,因此心裡有許多不滿,甚至有反抗爸爸的想法,但同信仰的大哥知道後,並不鼓勵我這樣做,所以只能繼續隱忍。
可能是缺錢的關係,爸爸總是叫媽媽去做些奇怪的手續,半挾持半威脅的說:「我是為你們好,我的以後都是你們的」,聽著他威逼勸誘的說服,我們也繼續忍耐。
爸爸有時會胡言亂語,我聽起來覺得怪怪的,不安全,我心裡暗自思忖,「此地不宜久留」並悄悄告知妹妹。妹妹很聰明,在離開前幾天,她就開始演練如何收拾物資,包括包包、重要物品、貼身衣物、卡片、現金等必需品。甚至在計畫執行當天,她還先把借的書還到圖書館,大膽的她,實在讓我無言….。
媽媽則只帶了一身衣服、一個包包、證件卡和一些現金。看著妹妹和媽媽,感覺根本不像要離家出走的人。
至於我,留下了第一次買的檸檬刨刀、舊眼鏡、一顆硬碟(裡面存著以前上課的筆記),以及一些屬於我的小東西:手機、信用卡、私房錢、證件還有買奶粉送的封口條,收集的環保吸管、所有適合吃甜點的小湯匙,還有電腦的硬碟與隨身碟。離開家之前,我看了一眼佛櫥,心想:「掛軸應該會被帶走吧。」於是,轉身離開。然而,掛軸並沒有跟著我們搬到阿姨家,讓我心懸著好久,好久,直到阿嬤過世,掛軸才回到新家。

過了一年又七個月,我終於明白,我真正能帶走的,是我半個家——我、媽媽和妹妹。而那些我沒辦法帶走的,仍留在原地,只是再也回不去了。唯一的遺憾,是患有重聽與失智的人瑞阿嬤,無法繼續走下去,也沒辦法得到延續的照顧。
上述這樣的無奈,我歸咎社會安全網的不足。因為不是每個人都知道社會安全網的存在,它的普及性不足。我曾遇到沒工作的緊急處置,只是讓我領三次失業急難救助,這對於沒勞、健保紀錄、無依無靠的人,有時候會累積對社會的不滿,可能選擇做一些傷人傷己的事。
我曾多次想走上那條復仇的路,但信仰始終拉住我。信仰告訴我:文化、世界、和平,一個人有一個人的文化,有他的經過,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。擦去一個名字,就少了一個故事。但事情有那麼容易嗎?
一個名字背後,牽連的是一個家庭,一個人際關係,一個工作環境,最後是一個人的生命歷史。如果這一切無法延續到自然謝幕,那麼社會安全網也就失去了它的意義和價值。對於人口日漸稀疏的社會,每個獨一無二的存在,如果只因無法「敗部復活」,那是件很可惜的損失。
這些議題,過去我只能默默思考,不願與他人談論。如果社會真的能給予更多支持,是否就能改變現狀?回想當初,我、媽媽和妹妹三人離家時,只能想「最需要的」,是落腳處、一點金錢與一身衣物,其他的都是奢侈。
如果能打造一個世界,不需金錢,只要衣物、藥品與個人水壺也能生活得很好,那就好了,那麼人們應該就不會再懼怕社會安全網的崩潰,也不會因不滿或絕望而走向毀滅,走向「絕望中的反撲」。
這是一個「沒辦法+沒辦法+無限次沒辦法」的困境,最後的抉擇是「寧為玉碎不為瓦全」,以回報這片土地,但我知道,仍有轉圜餘地——從教育著手,從提供資源,協助敗部復活開始。
你知道嗎?這世界上最容易當的是消費者,但當消費者無法再消費下去,問題就會浮現。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(SDGs)的17項核心目標中,如1(消除貧窮)、2(零飢餓)、3(健康與福祉)、4(優質教育)、8(體面工作與經濟成長)、11(永續城市與社區)、12(責任消費與生產),我認為如果以上這些都無法實現,那17「夥伴關係」也就無從談起。即使有4(優質教育),如果沒有基本生活保障,人們一直撞牆,最終也是會崩潰的,或是默許的…被現實逼到絕境。
總結代價:一個家的破碎,一段投機的孤獨,一位重聽失智的長者未被接住,但我還是沒有做出傻事,換來,三人失去一切,自由受限,只能寄人籬下,走向逐漸凋萎的人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