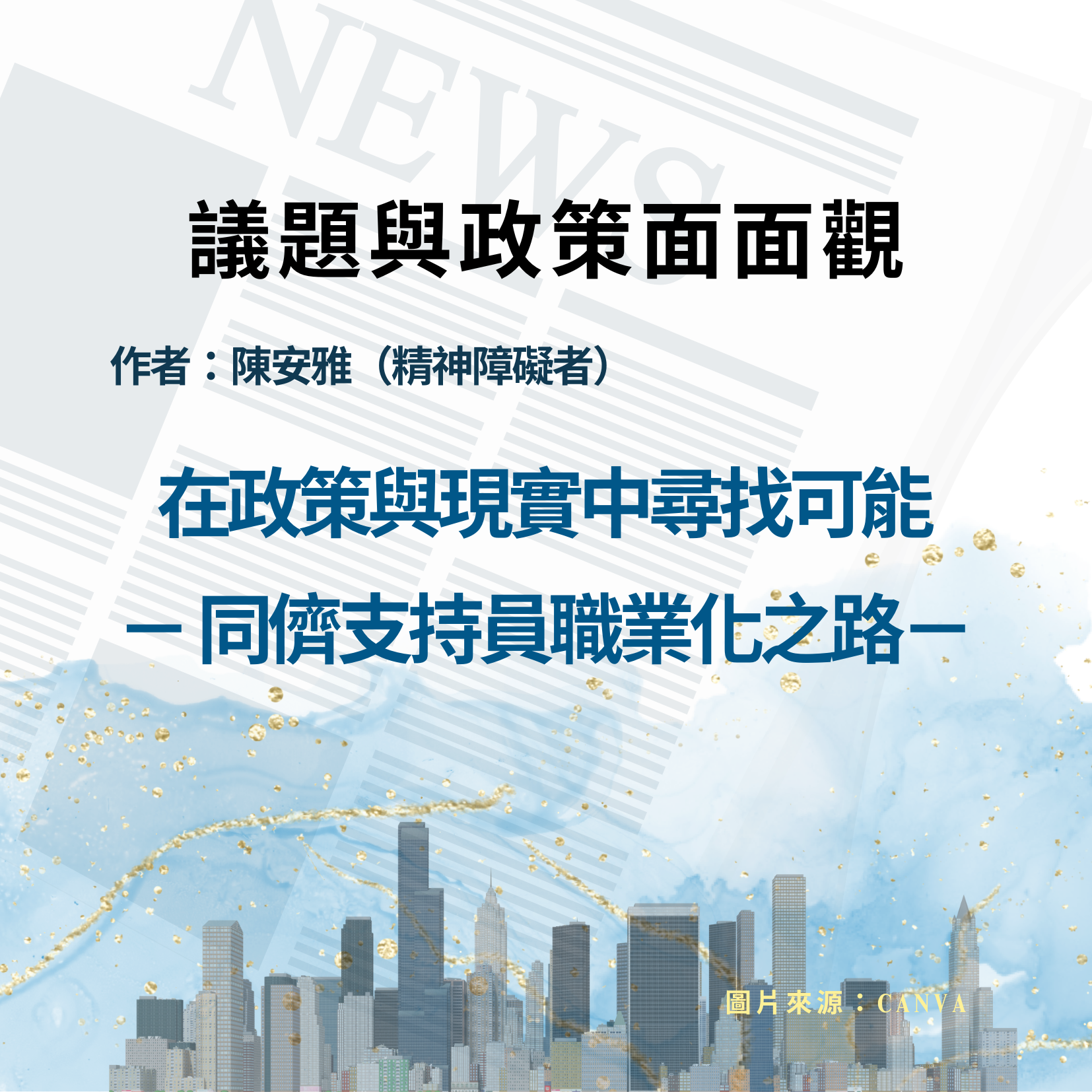文/陳安雅(精神障礙者)
當我們談論精神障礙者的就業困境時,社會往往關注的是「他們能做什麼?」、「他們適合什麼樣的工作?」而較少思考:「我們的社會是否準備好迎接他們?」在這次勞動部的拜會中,我更深刻地理解到,精神障礙者的同儕支持工作,不僅是一種服務,更可能是一項專業職業。然而,要讓這個概念被政策接受,仍有許多現實的挑戰需要克服。
壯職未酬|我的經驗看到「精障者就業」的限制
讓精神障礙者成為「正式助人者」,但國際上早已有同儕支持員的完整職業規劃。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,能在今年3月11日這天跟台社心一起去拜會勞動部,我發現「這是否可以是正式職業?」成為討論的核心議題。
目前在台灣,「同儕支持員」的服務鐘點費時薪約230元,與居家服務員相當。然而,在我們去年與台社心一起去參訪韓國後發現,與韓國相比,我們的制度仍不夠完整。在韓國,成為一名正式的同儕支持員,需要完成100小時的專業訓練,並通過國家認證考試,薪資甚至能達到與剛畢業的社工相近的水平(約4.6萬至5.6萬元)。
但在台灣,目前同儕支持員的訓練,僅需完成衛福部社家署公告的18小時,且這項服務的發展仍高度依賴政府補助,且每名障礙者每年僅能申請政府補助20小時的同儕支持服務。換句話說,這項服務並未真正市場化,也無法成為穩定的職業。若「同儕支持員」無法獨立於政府方案之外,它仍然被視為一種社會福利,而不是一個正式的工作選項。這也是這次會議最大的挑戰 —— 如何讓同儕支持員成為「職業」,而非單純的補助型服務?
職訓成才|訓後就業率:一個職業化的重要關鍵
我們很高興勞動部願意敞開心胸討論,並且樂見同儕支持員變成一種職業,勞動部最在意的是:「訓練能否就業?」,畢竟職業訓練的目的,就是促進就業。
現行職業訓練體系中,在一般的職業訓練體系中,訓後三個月內全職就業滿75%才算成功,但身心障礙者的標準稍有不同,只要有就業經驗(哪怕只有一天),就可以納入計算。
然而,目前台灣尚未有正式的「同儕支持員」職業訓練方案,因此政府對其就業數據計算和市場需求缺乏基礎資料。這次會議的討論方向逐漸傾向於:「或許可以先試辦計畫,收集供需數據,再決定下一步?」這讓我看到了一個可能性——如果能透過試辦計畫,建立更完整的同儕支持員就業模式,未來也許真的能讓這個職業成為現實。
高掌遠職|如何讓同儕支持員成為「真正的職業」?
在拜訪前,就在思考「或許很多人會問,這真的是一個正式的職位嗎?」
而後有了一個更深的體悟:職業是被創造出來的。
台灣過去沒有人會想到「心理師」會如同現在是一個如此普及的專業,如今在心理健康領域因為民眾心理諮商的需求增加,已成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同樣地,當精神障礙者不再被隱藏於社會之中,當我們逐漸意識到「受助者也可以成為助人者」,同儕支持員的職業化,就成了一個必然的進程,且同儕支持員並非是一個全新的職業,在韓國以及許多歐美國家,已經行之有年,我國目前推動,也只是跟隨其腳步,非高風險的開創先機。
當精神障礙者不再隱藏,而是開始尋求復元之路,這不就是一個「活化職業」的機會嗎?
這個過程,需要政府、企業、社會福利體系、以及精神障礙者本身共同參與。我們能否讓這條路變得更寬廣?我們能否讓更多精神障礙者有機會透過這個工作,重新找回自己的價值?這不只是就業問題,而是我們如何定義「精神健康」與「社會融合」的問題。
這次會議後,我也聽到三條可能的發展路徑,整理如下:
- 建立專業訓練與認證制度
目前的政府所規劃18小時職前訓練課程,與其他國家相比明顯不足,應擴增至至少100小時,並包含實習機制,讓學員能夠在不同場域中累積經驗。參考韓國、日本經驗,應建立國家級認證制度,讓「同儕支持員」的資格更具專業性與公信力,這正是台社心目前在推動的。
- 政策試辦,逐步推動正式職業化
政府應該考慮,透過1-2年的試辦計畫,與地方政府、醫療機構、社會企業合作,收集數據,驗證同儕支持員的就業可行性。若數據顯示穩定需求與就業率,則可向政府提案,將此職業納入正式職業訓練與勞動市場機制。
- 逐步導入市場機制,降低政府補助依賴
目前的同儕支持服務需求尚未被真正開發,未來可以結合企業EAP(員工心理支持計畫)、社區心理健康中心、醫療院所等場域,讓這項服務進入市場。透過「人力派遣模式」,建立專門媒合同儕支持員的社會企業,讓服務對象能夠直接聘用,而不完全依賴政府方案。
合職同方|同儕支持員設立,政府與社會雙雙獲益
對我而言,不僅僅是身為精障者發聲,同時在就讀社工系的自己,也會思考這個職業設立,除了對精障者有益處外,在鉅視的觀點裡,又能有什麼改變或助益。而我自己經過思考後總結成以下三點:
- 政府節省支出
同儕支持員的存在能幫助精神障礙者穩定就業、減少失業補助、降低住院率,長期來看,這是高CP值的投資。
- 社會勞動力提升
讓精神障礙者從「被照顧者」變成「助人者」,這不只是解決失業問題,更是讓社會多了一群有貢獻的人。
- 與國際接軌
歐美、韓國、日本都已經有同儕支持員制度,我國現在推行,不是「創新」,而是「追趕」。
- 真正落實《精神衛生法》第7條與CRPD
不只是符合國際標準,更是台灣早已承諾要做的事,現在僅是尚未落實。